筆者第一次親身體驗大規模的非國民黨召集的群眾抗爭運動,是1986年11月30日在臺灣桃園發生的「中正機場事件」,(中正機場已改名為『桃園機場』)。由於沒帶相機,故沒照片,只能靠文字描繪。畢竟自己照的、或照片中有你(別人照的),才比較可靠、才是更真實的生命體驗。
這次群眾運動是由中壢市中心的公園出發,步行經過田野,往桃園機場方向前進,目的是要去機場迎接黑名單之一的前桃園縣長兼美麗島雜誌社社長許信良(既被通緝、但又不准回臺灣的奇怪現象)。
由於參加的人相當多,故隊伍很長,雖然路程遙遠,但經過許多美麗的田園,感覺好像在健行。甚至在行進過程中,還覺得埸面非常壯觀且具有趣味性。當時覺得這麼美的景觀,竟然沒帶相機去拍照,甚至都覺得有些地方該錄影,因此以後,去參加街頭運動,就經常帶相機了。
底下即將事件發生的遠因、近因及其所呈現的美感與衝突描述如下:
中壢事件
1977年11月19日,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的投票日,曾發生了震驚海內外的「中壢事件」。由於選舉期間與投票過程有些不正常的活動、且開票時,不讓民眾監票,故許多人懷疑國民黨選舉作票,當時約一萬人憤怒地抗議、遊行、並包圍中壢市警察局,有一或三位民眾被槍擊傷亡、中壢市警察局火災。中央只好下令重新公開開票,並讓民眾監票。許信良才順利以23萬5千多票對國民黨候選人14萬7千多票的懸殊比數,當選桃園縣長,獲得壓倒性勝利。蔣經國在1977年11月19日中壢事件發生時的日記寫著:「難道只有選舉才算是民主政治?……但是又不能不辦!」
退報運動與媒體生態
中壢事件爆發後,所有報紙都被禁止刊登詳情,但耳語仍在各地相傳。週一,我在語言中心補英文,由於大多學員都是公務員選派出國進修的公務員,有位住中壢,他在下課提及中壢事件一點細節。
一星期後,突然《聯合報》整版刊出對國民黨有利的描述。桃園的人民看了之後,有許多人覺得非常不公平與不夠真實,因此,就發動「退聯合報運動」,紛紛將報紙寄回報社。誠然,在高壓政治下,報紙在政治報導與評論並沒有多大自由,但何以獨選聯合報,實在耐人尋味。
隔了十多年,聯合報又為了某記者報導某些事情,而解僱該記者,繼而打官司,但貧窮的小記者與國民黨政府保護且有錢的媒體打官司,怎麼會獲勝呢?加上臺灣當時司法人員百分之八十是為國民黨統治階級服務,只要用時間拖延方式……,小記者就受不了了。這也引發人們對報社內部自由、勞動權保障、及資產階級民主的流弊……等等,有關媒體與政治社會體制等問題的討論。
甚至引發由臺大法律系教授林山田等人所發動的「媒體改造運動」。他們到各校座談。但到了世新,卻遭到不太好的干擾、抵制,包括在小劇場外面及校園走道發一大堆傳單……等。據說,校方後來私下向主辦社團「道歉」。但抵制、干擾也沒用,因為參加的學生很多,照理說,在世新,晚上社團舉辦的活動,通常參與的學生不多,但這次卻例外。
由於1978年12月,臺灣原本正在舉行中央民代及縣長選舉,但由於中(臺)美斷交,因此蔣經國就運用緊急處分權,而宣告暫停選舉。隔年,余紀忠時代的《中國時報》以頭條新聞刊出「政府決定年底恢復選舉」,結果,由於蔣經國或國民黨高層的迫力,總編輯被更換。原本要辦美洲版(海外版)中國時報,錢被卡住,匯不出去,自然被迫停止。
標舉無黨無派的《公論報》則老是被找渣子,最後倒閉。
《自立晚報》更常發生政治迫害事件。我擔任世新第一屆專科生回校補大學學分的「倫理學」課程時,因為播放我拍照的各種街頭運動的照片,剛好提到五二〇農民事件,自立晚報記者採訪及被警方打傷之事,有位前任主管杜先生,下課十分鐘時,除了補充五二〇自立晩報記者的狀況,順便提到當年他任副總編輯時,有篇報導送到印刷廠排印,結果印出來的卻和他所編的內容不相同,他就打電話到印刷廠要求更正。結果沒多久,就有位「情治主管」打電話給他,請他體諒。他才知道就連報社內部的印刷工人都是「耳朵」,難怪「保密防諜,人人有責」、「隔牆有耳」除了是當時反共的標語、也成為反諷國內威權統治的流行用語。
在傳播學院有「媒體識讀」及「媒體批判」(普遍媒體的本質與其力量的有效範圍或極限的批判,非專指某媒體的內幕,但也可用現實世界的某些媒體作例子,來印證、否証)。但有些人學術程度欠佳,説:「你批不倒媒體的。」在臺灣,由於缺少基本哲學課,就連「批判」一詞的哲學基本意義都搞不清楚。例如:德國哲學家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並不是要讓理性倒掉,而是要告知「人類理性認知能力的有效範圍或極限在那裡」或「理性的功能有那些侷限」等等。亦即有些領域,理性是不夠力的,還需要靠感性、道德實踐行動……等,但後者的效力也有其限制,故也需批判。媒體報導通常是表象,而且離全部表象也一段距離,至於表象背後的根源性真相,都有待未來更深入的研究,這也不是單靠檔案公布就可全盤瞭解。只要涉及007情報員的故事、以及當事人的心態、思維模式……等等,就只能半猜測了。也因此,讓每一世代的人都有機會改寫。但下一世代要感同身受上一代對時代的感受,是不可能的。人對自己所寫的還是謙卑或保持開放性的修正比較好。
十二大政治建設
1978年3月21日,蔣經國當選總統。由於1973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提出「十大經濟建設」。相應的,在1978年年底的立委等民代選舉,「黨外」候選人們更進一步提出了「十二大政治建設」的共同政見,即(1)國會全面改選,省主席及臺北、高雄市長直接民選,(2)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3)反對黨工支配校園,(4)解除「黨禁」及「報禁」,(5)國外旅遊自由化,(6)解除戒嚴令,(7)廢止刑求,(8)實施農業保險、失業保險及全民醫療,(9)制定勞動基準法,(10)制定環境保護法,(11)反對省籍差別及輕視臺語,(12)政治犯的大赦等。上述內容也是1990年以來,臺灣一直努力的方向,有些內容已實現了。但由於12月16日,美國宣布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蔣經國乃宣布暫停選舉。
一般而言,在野的新思潮如果大方向正確的話,往往比同一時代的執政者要前進些,而且在日後會成為事實。而執政者常基於現實條件及既得利益較保守。歷史就在前進與保守的相互制衡中往前推進。但是在一個不太自由民主的社會中,有時提出較前進的思潮,會招來牢獄之災。上列黨外人士在隔年即發生了。
1979年1月21日,余登發高雄縣前縣長余登發以「為匪宣傳」的「叛亂罪」被捕,許氏為了抗議,乃參加1979年1月22日,高雄橋頭的抗爭遊行,這是戒嚴時期第一次的政治性示威遊行。不久監察院即以「未請假即外出」為理由彈劾許信良。亦即許信良當桃園縣長一年多後,即被迫離職,並於隔年赴美進修。上述事件已預告了國民黨內部守舊派勢力又進一步取得更多的權力。也預告了下一次的捕抓異議人士。
美麗島事件
1979年10月,由絕大多數的黨外人士合辦的《美麗島》月刊正式成立,並在各地設服務處,形成「沒有黨名的政黨」。但不幸的是,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黨外人士在高雄舉行「人權」大遊行。卻發生了軍警與人民的激烈衝突,而發生「美麗島事件」。
在該次政治事件中,在野人士主張解除戒嚴、不改選的國會議員必須退職、開放觀光……等,但卻有二百多位在野人士被約談或偵訊,三十多人被判刑,甚至有八位菁英人物——黃信介(當時的立法委員)、姚嘉文(臺大法律研究所碩士,人權律師)、林義雄(臺大法律系畢,時任省議員,和姚嘉文曾獲內政部頒發的優秀律師獎,因為他們共同開辦了平民法律服務中心,義務幫貧困的人法律服務或打官司)、張俊宏(臺大政治研究所碩士,時任省議員,當時的政治中心在省議會,而不是立法院,因為立法院中的不改選的「萬年立委」乃是表決部隊,是行政院的『立法局』)、施明德(陸軍官校,坐牢二十年,典型的政治犯)、呂秀蓮(哈佛法學碩士,曾任行政院科長、女權運動者)、陳菊(世新圖資科畢業、海外異議人士或黑名單人士與國內政治人物相互聯繫的重要窗口、人權工作者)、林弘宣(臺大哲學系畢業,曾留美,專攻田立克系統神學,牧師)等都以軍法中的唯一死刑起訴。最後分別被處以十四年、十二年及無期徒刑。審判期間的「二月二十八日」又發生了「二二八林宅悲劇」(即林義雄的母親及二位女兒均被刺殺,只有小女兒幸運地活下來,現在美國已大學畢業),一直到今日仍未破案。
審判到最後,由於氣氛的蕭瑟與正義理想的相互輝映,場面非常感人;因此連女法警與旁聽席上的平民都流下了熱淚,法官們也神情黯然。這究竟是誰的錯?是軍人?是這些「叛亂犯」?是審判長?是辯護律師?是凶手?這一切都不是!是那充滿結構性暴力的戒嚴體制!是那封建心態!是那僵化的教育體制與被控制的傳播媒體!只要是敏感性政治新聞就被某些媒體扭曲。它們才是背後的大罪人!
「美麗島事件」之後兩年,臺灣恢復選舉。人民的生命力迅速復甦了。那一場軍法大審震醒了許多人對現存社會政治體制獨斷的美夢,無論是執政的、中立的、知識分子、本省人、外省人以及各階層的人。因而受刑人的家屬如周清玉(姚嘉文之妻)、許榮淑(張俊宏之妻)、黃天福(黃信介之弟)……等都高票或最高票當選中央民意代表。
但是我去林森北路新福宮(主祀新丁公)廣場聽周清玉的競選演說。到附近時,看到穿制服的警察,卻感到一種緊張肅殺之氣,一直到走入同溫層的人群中及聽眾報以熱烈掌聲,才暫時稍稍驅走美麗島事件,尢其新二二八林宅案所帶來的冰冷肅殺之氣。那種氛圍,很多下一代、下下代的人是很難感受到的。亦即晚上的街道與天空怎麼會有冰冷肅殺之氣呢?就如同電影,常用天空灰濛、冷風颼颼、旗子異常飃動來象徵「秋決」的氣氛……。
陳文成事件
1981年7月3日早晨,美國卡耐基美農大學(統計學領域,世界排名前三名的大學)數學教授陳文成教授(1950-1981,當時只有三十一歲),只因為在美國捐錢給美麗島雜誌,在回臺後,被警備總部約談。約談後的當晚深夜,很可能被另一系統的特務、或其他極右翼的法西斯分子、或其他組織,暗殺於臺大學生活動中心旁的草皮。臺灣的御用媒體卻宣稱是「畏罪自殺」,甚至設法醜化陳教授的道德人格。但陳文成原本在隔月赴美後,仍有一個美國政府委托統計學界的大計劃必須主持,因此不可能自殺。
國際媒體對此事的反應很激烈,《新聞周刊》、《時代》、《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美國著名的雜誌、報紙,都將此事結合國民黨特務在美國大學校園內的間諜活動加以報導。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洲太平洋問題小組則於7月30日召開「聽證會」。聽證會以「國民黨特務與陳文成教授事件」為題,要求美國政府採取行動,制止國民黨特務在美國活動。最後,由小組主席索拉茲議員提案:「修正援外相關法規,立法授權總統,對於一貫威脅、迫害美國公民的國家,停止輸出武器。」此案於翌年(1982年),加入美國武器輸出統制法修正條款內,並通過,這使國民黨當局相當頭痛。
2021年9月28日,臺灣大學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 「三一矮牆」的題詞「紀念一位堅決抵抗國家暴力的勇者」,正式完成安裝。此處的「三一」意指三十一歲。
江南案
1984年、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以學術研究方式先寫了一本具有批判性的《蔣經國傳》(其博士論文)。其後,又準備寫《吳國楨傳》。由於吳國楨(1903-1984)清華學校畢業、留美,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畢業。曾任上海市長。來臺後,在擔任省主席時,常與省黨部主委蔣經國爭執。其座車常剎車失靈及被動手腳,很明顯是意圖製造車禍或其他意外,因此吳國禎在宋美齡協助下,離臺赴美,一到美國即登報大批國民黨。也可說《吳國禎傳》有許多不利於蔣經國的資料。但江南卻於10月15日,被臺灣情治單位派出去的「竹聯幫」成員,暗殺於美國舊金山的郊外住宅。同時,有關前省主席吳國楨的資料也全部被燒燬。由於江南擁有美國籍,再加上被刺殺於美國本土。因此美國政府非常憤怒。臺灣政府乃將情報局長及暗殺者等人判刑。但也有人認為上述表象背後的真正原因是與蔣家後代有關。更深入的真相為何,至今仍不清楚。
歷來政治暗殺的事實真相,幾乎都要等二十多年後,才可能知曉,甚至也可能永遠交代不清楚。因而歷史學家又有很多事可去旁敲側擊。
自由時代
1984年,中華民國仍處於動員戡亂時期軍事戒嚴,鄭南榕(創辦人)與陳水扁(社長)、李敖(總監)等友人創辦了黨外運動雜誌《自由時代周刊》,口號是:爭取100%言論自由。
先把臺北街頭場景拉到五十年前1949年的5月19日,國民政府臺灣省主席陳誠在這一天頒布「戒嚴令」,沒想到一眨眼三十多年過去,任憑世界局勢與臺灣社會如何快速變化,這項嚴重箝制臺灣人民言論與集會結社自由的戒嚴令卻仍屹立不搖。
1986年5月19日,鄭南榕、江鵬堅等人首度在有「民主聖地」之稱的臺北「龍山寺」靜坐十二小時,當時龍山寺擠滿了民眾,要求執政當局廢除已實施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此項活動引起國際媒體的重視與報導。1987年1月24日發起「平反二二八」的活動。雜誌也曾刊登蔣經國由於糖尿病,坐輪椅,眼睛不太好的近照、臺灣共和國的憲法草案……,總之,衝撞當時所有的禁忌。1989年01月21日,高等法院檢察署簽發了傳票給鄭南榕,指控他「涉嫌叛亂罪」。傳喚其到庭。但屢傳未到。1989年4月7日,中山分局刑事組在侯友宜帶領下,包圍其民權東路三段的住屋,鄭南榕拒絕被補,而自焚於家中。
返鄉運動
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在臺北市圓山飯店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江鵬堅擔任黨主席。
美麗島事件後,在美國的鄭紹良、許信良、陳婉真、謝聰敏、孫慶餘、陳昭南,胡忠信、陳芳明等人,共同辦《美麗島週報》,持續五年多,在民進黨成立後,許信良等人將他們在美國紐約建立的臺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改名為民主進步黨海外支部。並透過美麗島週報聯絡友人,推動1986年的海外黑名單返鄉運動,希望能夠透過此強行返回臺灣的運動,衝擊或改變國民黨黑名單的政策。11月14日,民主進步黨海外組織代表團的第一批的7人於上午7時搭機抵達桃園中正機場,但未能入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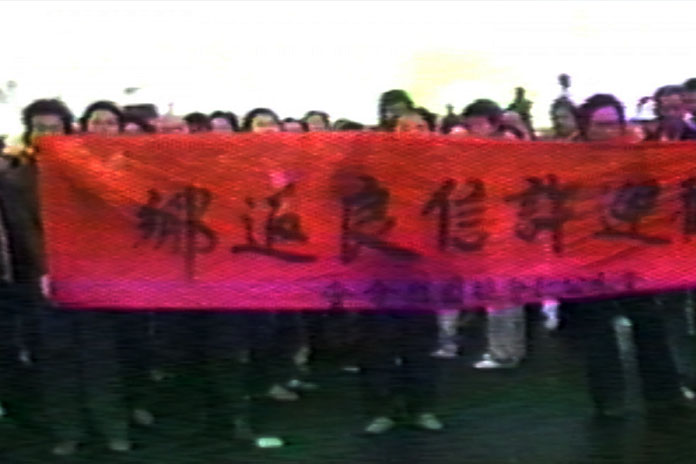
1986年11月30日月,國內正在舉行立委與縣長選舉,許信良、鄭紹良等人為了突破黑名單的禁忌與幫黨外人士造勢,企圖搭機至中正機場企圖闖關回鄉(按:此次費用與美麗島週報的費用大多由航太專家鄭紹良支援)。當時全國各地有二萬多民眾(桃園人居多)到中正機場支持許氏,並要求政府能讓黑名單人士順利返鄉。他們由中壢市公園出發,步行約二個小時至機場去迎接老縣長。
民眾所走的路線主要是較偏僻的產業道路,而不是車子太多的大馬路。由於大部份都曾當過兵,因此就像軍隊行軍似地自動分成兩列,沿著道路兩旁前進。走了約一小時,開始進入車子相當稀少的郊區,因此有些人及自動排成三人一排的小隊伍。在小隊伍之前還有掌著大旗的引導者,有的人則拿起小喇叭吹奏進行曲,當然也有人身上披著顏色鮮豔、充滿喜氣的彩帶。他們沿路唱歌、答數,並親切愉快地和桃園客運汽車上的乘客微笑打招呼,乘客也報以會心與鼓勵的微笑。
總之,非常類似軍隊行軍時的情境。但不同的是:軍隊靜悄悄的帶背包、槍等軍事裝備,充滿嚴肅之氣;而他們由市中心的公園出發時,卻是鑼鼓喧天、長串的鞭炮聲不絕於耳,尤其走路時的神情更掩不住內心的喜悅與興奮,一切的一切是顯得那麼的喜氣洋洋。
其中最令人難忘的景觀是:當民眾來到機場大廈後面盡是綠油油、廣大「無垠」的田野,約三公尺寬的泥土略微蜿蜒曲折。民眾有秩序地沿著道路兩側、曲曲折折的徒步前進,隊伍從山上延續到高速公路的盡頭,而機場大廈就矗立在數公里外的田野旁。
從山上往下俯視,令人心情開朗如明月,並感到這幕雄偉壯觀的情景就好像在電影中有一批軍隊沿著鄉野小徑靜悄悄地偷襲那棟神秘的大廈。
這一切的一切構成一幅以遼闊清純的大自然為背景,去烘托出整個活動的雄偉壯觀、動態立體、理性與人性交織,以及黃褐色、草綠色與各種不同衣服的顏色對比而成的藝術景觀。這種情景在一般的都市遊行,根本不可能形成,當然隊伍也不可能那麼漫長,並全部映入眼簾。
在這過程中,軍方的坦克開動了(此乃從電視看到,因裝甲部隊原本就在湖口),鎮暴部隊、鐵絲網、拒馬層層擋在高速公路上;噴水車噴出了紅色的水,人民與軍警的石頭滿天飛。因郊區非常空曠,故這一切構成另一幅動態美麗的圖像。
不過,被控制的許多傳播媒體卻一面倒像國民黨政權。當有些人民的衣服被紅水染紅時,這些御用媒體竟然報導說這是由於人民自己帶了紅油漆,故意染了自己,意圖嫁禍於軍警。
但就鎮暴理論而言,鎮暴部隊採用紅水,原意是噴向特定的違法人士,以當作記號,方便逮捕,換言之,使用紅色的水噴民眾是事實,只是技術不純熟。事實上,也不可能如理論上所說的,噴的那麼準確。好在外國的電視記者從軍警後面攝影存證,才揭穿了當年臺灣部份大眾傳播媒體的謊言,畢竟較完整的錄影帶總是比被編輯或報老板修改後的文稿真實。此外,當時的自立晚報發揮了道德勇氣,首先報導了許多事實真相,才使得這項假新聞不再被任意渲染下去。
由於「中正機場事件」我沒帶相機,覺得有些遺憾。因此以後,去參加或觀察街頭運動,就常帶相機。但可惜的是,後來的街頭運動都是在市區,永遠沒有寬闊田野與人羣互動所構成的美感。但是也留下了一些歷史境頭。更重要的是,幫許多學生留下青春時代、熱血沸騰、正義感特別強烈的人生階段的部分珍貴身影。雖然有些照片被臺北市莫名奇妙的淹大水毀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