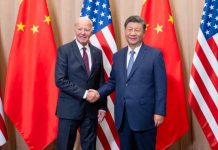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將在12月9和10日以美國為首舉辦「全球民主峰會」(Summit of Democracy),這回邀請了110個國家的代表,臺灣有幸也被邀請出席盛會。然而,就是因為邀請了臺灣,卻沒有邀請中國,造成了刻意以「民主」之名介入臺海政治的爭議而鬧得沸沸揚揚。

自從美國在阿富汗狼狽撤軍之後,這個全球民主峰會的舉辦便蒙上複雜的政治意涵。首先,很明顯的是,美國意圖在內外危機四伏的條件下重振雄風、招朋引伴,重建全球霸權和領導地位的政治活動。受邀的國家從老牌民主大國 (如英、法)、近年來民主制度建立有成的立陶宛、捷克等,民主有成但遲緩前進的臺灣、南韓、印度等,一直到未來希望拉攏的剛果等非洲新興民主國家。
其次,特別是針對圍堵中國、俄羅斯等國的印太區域戰略而特別動員了許多亞洲國家,諸如東亞第一島鏈的臺灣、日本、南韓,以及東協(ASEAN)的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等。未受邀的則是中共、俄羅斯及其與之友好的越南、泰國、新加坡、緬甸等。美國以民主之名,卻實質上偷偷玩起二十一世紀反中抗俄的新冷戰。
本次民主峰會聚焦在三大主題上,分別是:對抗威權、打擊貪腐以及促進對人權的尊重。這個歷史階段的全球民主議題主要是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市場失控、科技擴張和國家失敗的狀態,全球貧富差距拉大,財富和權力集中在掌握金融與科技的少數人手裡,造成威權治理、貪腐和人權剝奪的現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臺灣被鄭重邀請是至高無上的榮譽,它表示臺灣自從解嚴後三十年來的民主轉型經驗被高度重視和肯定,並因此有機會將民主成果分享到國際社會,浮上國際檯面上為自己發聲。
民主峰會的實質是,相較於亞洲其他國家,臺灣的民主經驗有其特殊性和代表性。首先,作為全球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典型代表,臺灣和平式的、不流血的民主轉型經驗被高度肯定。它包括了如何從軍事戒嚴的軍政府轉型到文人政府,如何建立反對黨而形成正常的政黨競爭體制,如何從黨政軍全面監控轉型到尊重差異的言論與思想自由,甚至,如何經歷三次政黨正常輪替的政府治理等。相較於經常政變和體制崩潰的菲律賓,臺灣確實是個新興民主模範生。其次,解嚴後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造就了多元化的身份認同、非政府民間組織和諸種異見,而在強調民眾參與的政府治理改革中,逐漸建立了由下而上的「公民主義式國家」。它包括了:各種民眾參與式的預算審查、民眾參與式的市政決策體制、審議式民主決策模型、開放政府、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一直到近來的地方創生運動等。相較於東亞新興民主國,臺灣的民主乃是奠基在公民自主參與和審議的基礎上,確實超越了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的典範和經驗,超越選舉政治,呈現了文化多元主義的色彩。
再者,在人權發展議題上,臺灣是少數人權最為活躍和最被保護的地方。人權是國家恆常關照的主軸,並設有國家人權委員會作為常設機構。舉凡關乎身份認同的族群、階級、性別和性認同則都有代表可進入國家決策過程來做審議。近十五年來性別主流化運動在國家體制中的試煉,造成女性地位的提升,甚至有亞洲第二位女總統的誕生。2019年還通過了「同性婚姻法」,以法治來支持同性戀者的結婚權和家庭權,可以說是亞洲LGBT人權保護的典範。以上是臺灣這三十年來最值得驕傲和對外輸出的重要民主經驗。
然而,這回的民主峰會也有其虛妄之處,背後多國際政治的糾葛和拉扯,以及中美兩強爭霸之下的妥協和折衝。以這回臺灣被正式邀請,但總統卻無法親自出席這件事看來,沿用「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APEC)模式正是中美角力下的妥協之舉,這是為了避免踩到美中共識下的一中原則和臺灣關係法的紅線。而臺灣能派出的代表也只到駐美代表蕭美琴和行政院政委唐鳳兩人,派出代表層級太低,表示臺灣的國際政治實力不足因而無法介入外交折衝的問題。如何避免淪為美中爭霸下受人制約的棋子,而能擁有臺灣的自主性,是參加民主峰會應當思考的事。
其次,是需要重新思考當前的國際情勢,重新置位美國在當今全球領導權的地位。當今的美國已經不是1980年代全盛時期的美國了。在全球化的市場失序和國家失能的狀況下,美國有許多內在即刻卻拖延許久的危機需要處理。諸如: 貧富差距擴大、基礎設施破敗和不足現象、企業逃稅而導致國家財政危機、健保和醫療保險制度的不足等;更不必說,近兩年來的疫情衝擊和貿易戰所導致的高度通膨現象。對外則有中國崛起所引發的領導權危機,阿富汗的倉皇撤軍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罷了。臺灣當局需要重新評估加入美中新冷戰所要付出的代價。
美國在打解放黑奴戰爭時,領軍的林肯(Abraham Lincoln)將軍和士兵們有一段對話,值得深思。士兵在戰事節節敗退的關鍵時刻,詢問林肯將軍正義的問題。林肯說:「不要問正義是否站在我們這一邊,而要問『我們是否站在正義的那一邊』。」回訪民主峰會議題,站在民主的那一邊,既是歷史也是真理的選擇。然而,選擇民主,是為了拓展光榮的經驗,為了交更多的朋友,更是為了擴大影響力範圍,保存優良傳統,同時惠及他人,而不是拿著民主旗幟來製造敵人。甚至,我們不應該只是抓住民主標籤,而是要進一步思索近年來「過度民主」所造成的「民粹主義現象」如何反過來吞噬民主國家的穩定和繁榮,造成耗時費力又無效率的民主問題。意味著,民主峰會更應該重新思考民粹主義,討論如何從選舉形式的民主,進步到可以「深思熟慮的/協商式民主」(deliberate democracy)。
筆者認為,臺灣未來也應當想方設法地與中國進行和平的民主對話,將民主推行到中國去,而不應該跟著美國進行二元冷戰對抗,或者因投入新冷戰而進入軍備競賽的陷阱。如何清醒地參加全球民主峰會,輸出光榮經驗,同時又不陷入兵兇戰危的險境,是臺灣當局應當具備的政治協商智慧。